橋仔餐桌 一座生活博物館的體現
作者:謝仕淵 (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)
橋仔,馬祖北竿的一個小漁村。今日的橋仔碼頭通常停了幾艘小船,捕抓定置網漁獲的船隻,噸位甚至比1950年代美援時的機動漁船還小。石頭岸壁鑿下幾個繫船鐵環生鏽了,已很久沒有綁牢返港的漁船。2020年,橋仔只剩一戶漁家,一日兩趟依著潮水撈取洄游而來的海鮮,黃大哥的助手是一位外籍漁工。
橋仔曾是北竿漁撈與商販功能最暢旺的村子,除了來自福州周遭各縣的人,還有閩南與莆田的移民,利之所趨,眾生匯聚,來自各地的神明,比現居村民還多,橋仔的人口,已比戰地政務時期開始統計戶口時還少。那些在耆老口中說出的過往,一鍋又一鍋的蝦皮與丁香,驅動全村男女老少各自分工。
但那不是自由來去的時代,軍管限制了漁民馳騁於大海的能力。關於這座港的故事,出現在報紙中的,有則身陷迷霧、失去動力,但卻靠著觀察海象辨位,而未穿越兩岸的界線,船長因此而獲得稱頌的報導。那時確實有個案子,是關於北竿漁民到對岸做生意而被捕入獄,馬祖是冷戰的前哨戰。但,聽朋友說著那些餐桌上未曾少過的食材,便能了解報紙上不能說的,民間都有因應之道。
蝦皮終究開始少了,到臺灣賺錢最容易,臺灣經濟成長率上漲,馬祖人口持續外流,漁村人口少到沒有了觀察鯷魚習性而佈置的鯷魚樹,少到沒有辦法組織大型圍網船,少到無法經營釣取石狗公或石斑等高級漁獲的延繩釣。黃大哥的三張定置網,依潮水誘引而來的是黃魚、帶魚、小卷、肉鯽、白鯧等中游層的漁獲。

在水蓮大姊家,那張放滿一桌好料的餐桌,如同展演生活的展場。紅糟鰻、佛手、炸鯷魚、淡菜、章魚、紅糟雞湯、炸鯧魚、嶸螺、炸帶魚等料理,即是馬祖料理的特色,一張與海洋資源關切密切的餐桌,如同橋仔的生活永遠無法脫離大海,各家私傳的無人島中的筆架與嶸螺,以及如何在約莫20公尺的海裡,佈置各種洄游性魚類的網具,都是橋仔人必備的生活知識。
她談到捕撈蝦皮的故事,秋天後的蝦皮與春季的丁香,都是必須加工才能賣出的漁獲,進而牽動漁村整體的人力配置。馬祖在1950年代起,每年約有兩千噸蝦皮的產能,是數一數二的重要產地。不過1980年代初期,只剩下幾百噸。丁香與蝦皮上岸後,必須搶時間,全家動員,煮熟以讓漁獲停止腐敗,之後,放在竹席上晒乾,汰除雜物,最後賣給來收購的商人。每個程序,水蓮大姊都曾參與,她還曾去幫來自臺灣的商人煮飯與洗衣服賺錢。
那些年,她十幾歲,正是蝦皮盛產的高峰期。這個有人講馬祖話、閩南話,甚至還有人說莆田話的村子,因此充滿生命力,人口達於鼎盛,兩個泊船澳口忙碌非常。水蓮阿姨說那時連煮完丁香與蝦皮的鹹汁,都是製作各種kê(膎)的好材料。大海的恩澤跟漁村的富庶,來自於所有的物盡其用。

三十年來,橋仔已不再煮蝦皮,但我們找到許多廢棄的魚灶,不同時代、不同尺度,有的已頹圮、或者被覆蓋,但仔細看,還是依稀能辨識原來的痕跡。已經荒廢在家屋旁的老甕,則是陳釀蝦油的器皿。
經過追問下,水蓮姐後來拿出了醃製的小卷與苦螺,以及最後登場的蝦油,是那餐最無法忘記的滋味。比起淡菜、黃魚與紅糟鰻,滿溢腥鮮味的kê和蝦油,都是充滿風險挑戰顧客底限的食物,餐廳上也較少見,水蓮姐一開始也沒打算拿出來給我們吃。
一輩子都在打漁的黃大哥,皮膚黝黑但雙手手掌都被海水泡的發白。在他的口述中,一碗米飯配上一碗老酒、幾口kê,或是一點食物沾點蝦油,就變得有滋有味。他們的故事裡,這股鹹味,經常搭配著辛苦生活。其中的情節,苦跟鹹只有一線之隔。而那正是大海的滋味。新鮮帶脂肪的剛離岸鯷魚,洄游了大海,吸取了所有海味的精髓,然後醃製三年而成的蝦油,陳釀了最富層次的海的韻味。

後來,漁村的飲食生活,因為冷凍庫,而成為可計算、可延續的形式,不再只是靠天吃飯。沒有冰箱與冷凍庫,萬般從海裡來的東西,不是成為醃製物,要不煮熟晒成乾。有了冷凍庫,即使魚丸與魚麵製了大批量,冰起來,也能慢慢吃。捕魚的黃大哥,也能靠冷凍庫調節漁獲,避免魚賤傷魚。或者他們半夜出海,上岸後,也不必像年少時,急著賣掉,魚能冰一下,人能休息後,下午再運到塘岐賣。冷凍庫讓生活節奏不被魚腐敗的時間追著跑。
許多馬祖人,住在臺灣的時間都比馬祖還長,但只吃得慣馬祖來的魚,訪問好多人,冷凍庫都放滿了一袋袋準備寄給臺灣親人的海鮮,冷凍庫的發明者,應該沒想到,食物保存也能保存記憶。
橋仔餐桌,那些豐盛的海味,存有時間的痕跡,也體現人情的餘韻,是生活中具連續性的紀錄系統。以餐桌為核心,串聯的是從產業與分工、味道與記憶、生活與情感等一組組當代博物館關心的問題。餐桌的生活性,使其成為居民共作,甚至展演馬祖文化的日常平台。於是,橋仔餐桌如同一座座的展櫃,而橋仔更像是一座生活博物館的體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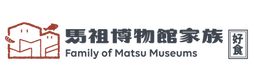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