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祖辭典之十:栽菜
作者:劉宏文
吾鄉僻處海隅,地磽水薄,不產稻米高粱,只能種瓜果蔬菜。吾鄉人稱種菜為「栽菜」,一詞多義,可以指栽種蔬果的辛苦勞動,也可以是身分識別,務農之意。我讀小學,有一回填家庭資料,家長職業欄我寫「種菜」,老師皺了一下眉頭,但也沒說什麼。在吾鄉,許多人名字都嵌有官、福、增、利、俤、金、花、菊、蓮…等字,前面帶個「依」,就是乳名了。你要打聽某人,同名的村子裡就有好幾個,只消冠上「栽菜」或「討海」的依福、依增,大家就明白了。
吾鄉人常說:「菜是水變的」,又說「栽菜無功夫,糞桶拿去箍」,可知挑水、擔糞皆是重活。有幾年,島上冬天乾旱,吾村家家都種菜維生,尤其缺水。父親就到隔鄰清水村租地種大蒜,那塊地在清水街尾,當時的農試所也在附近。父親目測山形,度量水脈,就在田畈邊掘了一口井,套入兩個汽油桶,水就汩汩湧出。那幾年的大蒜有半人高,莖粗葉厚,「三株蒜就秤一斤!」父親說。
我幼時去同伴家玩,在屋裡嬉鬧,總被大人告誡,不要打破床底下的瓦陶尿(夜)壺。吾鄉冬夜苦寒,用尿壺固是求方便,其實是肥水不落外人田,要留著施肥。父親歇手不種菜來台,有幾年跟我住;屋旁一塊空地,他看了手癢,三兩下闢成菜園,照時序栽種瓜果蔬菜,一刻不得閒。家裡的鮮奶罐就成了他的尿壺,在後院排成一列,甚為壯觀。有幾次我勸他用化肥,免得臭騷味惹鄰居閒話。他卻說:「尿素沒料!」我看菜園裡兵強馬壯的香蔥、茼蒿,風吹過一片有機綠意,都在點頭支持他的論點;我只得噤聲,繼續提心吊膽等著鄰居來敲門。
正月過新年,冬日寂寂,農事不忙,村人窩在家製扁擔、編籮筐、箍水桶,把去年收的菜籽,慎重其事地翻出曝曬,喚醒胚芽,春來好播種。蔴竹削成的扁擔,中寬尾窄,一道弧線淺淺地彎向兩端。尾端掛物處做成直的、勾的,挑時隨重物上下律動,咿呀咿呀地輕響,把力量傳達到極致。幼時看婦女井邊挑水,田塍澆菜,走起路來搖曳生姿,真是阡陌朗朗,一片清和。扁擔用久了,竹面就轉成光亮的褐色,竟是和竹簡很像,只是一個以文字刻寫,一個用汗漬染成,斑斑顏色都是歷史的滄桑。
二、三月開始種瓜,有絲瓜、冬瓜、南瓜、香瓜、菜瓜…,也種青椒、茄子、番茄及洋蔥。瓜果只需沃水澆糞,二個月可摘採。在枝葉下鑽進鑽出尋瓜果,要著長褲長袖,花粉葉毛會讓你全身發癢。父親說,颳風與炎日皆不適採茄子,因手臉會紅腫,但茄子好吃。村裡金泉伯獨居,他將整條茄子煨在飯裡,蒸熟了撈起淋醬油,吃得嘎吱作響。紅樓夢有所謂「茄鯗」,烹煮料理非常繁複,原來珍饈也可以是尋常食物。
四,五月以後,種四季白、紅根菜(菠菜)、荇菜,這些菜炒了會滲出紅汁,非常適合澆些老酒燜煮,吃時每每讓我想起詩經關雎說的,「參差荇菜,左右采之。」但詩經的荇菜是長於溪岸清水的野菜,不知古代窈窕淑女摘來吃食,有否以老酒調味?
七月蔥、八月蒜、九月栽蕗蕎(馬祖話音「ㄌㄧㄡˋㄊㄧㄡˊ」)。菜仔有些是去年留種收的,有些託人在台灣購回。幼時家裡有一本介紹各類蔬果品類的目錄,父親稱為「菜書」,好像是舅舅從台灣攜回,彩色版,村人常來借翻,是我們家的寶典。書裡光是包心白菜就有賓光、理想1號、2號…等五六種。有一年,翻到一頁香瓜圖片,模樣長得「高富帥」,就急急寫信,請台北念書的舅舅上迪化街買了種子寄回。滿懷希望的種下,出土、發育一切如預期,星狀葉子,爬籐蜿蜒,與鄰居田畈種得一個模樣;等到結了果實,表皮有一些紋路,心想可能是被蟲蟻叮咬爬行留下的印痕,也沒在意。後來覺得不對,每個瓜長得碩大飽滿,但都有網狀的紋路,像爬滿全身的筋脈血路,沒見過香瓜生得這般醜惡可怖。剖開,肉色像木瓜,大膽咬一口,香味妖嬈濃郁,與黃金香瓜的清香不同。沉沉的挑到市場,也沒人識得,賣不出去,我們是全部倒掉;那應是馬祖最早一批的哈密瓜,沒想到下場如此。後來在台灣見到,隨口問一下價,比隔攤的香瓜還貴。我以後不大買哈密瓜,想與此有關。
十月以後秋風起,蕭颯有寒意,開始種大白菜。父親掘土畇地,一條條的田畈,條理分明,熨燙服貼地像冬天的被褥。種大白菜要先育苗,在黑肥的田畦裡撒下種子,蓋上厚厚的芒草,白色的花絮在田埂飛舞,兩三天後,像雀嘴一樣的新芽萌出,再幾天已能巍巍站立,幾株一起,兄弟一樣移到掘好的窟裡,最後汰掉萎蔫不振的殘株,留下最為雄健的,從此盼望結實成果,賣錢換米;吾鄉早年,每村也總有幾個少年,或因種種緣由,陽光雨露都分給其他家人,從此留在島上,枯草斜陽,荒荒度日,成就了兄弟姊妹,沒有委屈、怨言,心裡仍是一片喜意。
大白菜採回要撕去散擴的外葉,煮了餵母豬可以增奶。餘下的菜梗雕成尖狀,紮上草繩以護住內球。有時農忙好收成,我也會隨父母挑菜到鐵板、山隴的市集,福澳偶而也去。村人前一日都會約好,幾家一道,備好手電,凌晨即起,結伴挑菜上路。吾鄉黑夜分外寧靜,遠處兵營犬聲吠吠,近處海岸濤聲陣陣,一群人在山路上喘著重氣;繁星如沸,雲漢浩渺,生活雖然艱難,自有里巷人家的清平安穩。吾村人在市集沒有攤位,挑去的農貨都要盤給「鋪家」。價錢好時,山隴的鋪家凌晨三點已在福澳嶺等者,村人一到,便搶過擔子一路挑到市集。菜價賤,也概括承受,甚少賣不出去原擔挑回。買賣彼此以誠相待,真是民間有信,嘉禮自在。
吾鄉缺水,土地貧瘠,可種出的白菜、菜頭(蘿蔔)卻又脆又嫩,清甜多汁。菜頭生得皮薄肉厚,不等一刀切下,就已喀嚓一聲,裂成兩片。切下來的菜頭片,薄薄的,晶瑩雪白,小孩當零食吃,田滋滋的,簡直就是鄉間的水果。菜頭可以素炒紅糟,或切絲炒蒜苗,雪白的蘿蔔絲中,摻著紅糟綠葉,好看又好吃。菜頭熬排骨,燉羊肉,慢火文個二、三小時,可吃得一家人油光滿面。
幼時母親訓誡我們珍惜飯食,常說遠房舅公家人丁興旺,食指浩繁,每日三頓根本沒有配菜。飯前舅公在飯桌上撒下一把「菜脯仔(蘿蔔干)」,連個碗盤都省了;十數雙筷子同時伸出,好像群雞爭食!貧窮若此,哀愁到讓人痛惜,但也沒有滅了人的志氣。吾鄉種的菜頭,根鬚在貧瘠地裡擴延逶迆,汲取石縫土粒中微薄水氣,終於長成日本人說的「大根」;經北風霜過,像白菜、大蒜一樣,都會滲出甜味。原來萬物在逆境之下,都能自尋出路,激發出最為良善堅韌的本質;就像吾鄉許多人,小學、中學畢業,即跨海來台,轉山過橋,度難解厄,於今散居各地,也都已是堂堂正正的人物了。
轉載自馬祖資訊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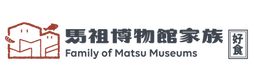

Comments